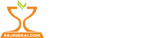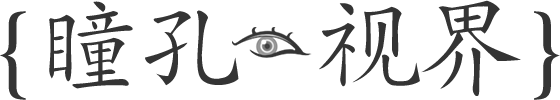一
二零一六年五月六日,礼拜五。
一场瓢泼大雨来得太过突然,刚下班回家时只感觉到身上点点滴滴稀疏的冰凉,忽然整个天幕都闪烁起来,像是谁在放映三十年代的老旧胶片,接着几声惊雷,禽鸟低飞。有阵狂风带起了地面的扬尘,可它还没来得及侵染人的衣襟,就先融入漫天的雨帘当中。风和雨交融成白色的魅影,席卷着这世界无尽的尘埃,在街道霓虹灯的映照下汇成条条有声有色的溪流,最后深深地、深深地坠入这喧嚣都市的下水道里。
在公司回我廉租房的路上有一家装修颇为典雅的草木小铺,不到三十坪的店里错落地摆满了漂亮的绿植和多肉,用紫外线灯精致养护,比外面要贵出不少,期间甚至有许多植物种子经过包装,能以成倍的价格卖出。店主小满与我年纪相仿,是个极好的人,在店里设置了卡座,低价提供咖啡甜点,也算能让人在价格上找到心里的平衡:“你看我这里不止买花,要是觉得花儿贵,多来坐坐就好。”平时常有年轻人贪图酒水低廉的价格和别致的环境而留恋于此,选择在这向那些偏爱萌肉的女孩儿们表白的男生不在少数,久而久之,这间不大的店里也增添了一抹古怪的浪漫氛围。
不过现在,店里更多的是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弄得措手不及的路人。着急忙慌打电话者有之,皱着眉不耐烦地点烟者有之,恬静淡雅窃窃私语者也有之。我进铺子找了个角落地方,不顾被雨水沾湿的头发,靠着墙按摩脖颈,缓释对着电脑一天后身体的疲倦。铺子里地中海日历上的那块“6”缺了,不知散到了哪里,我盯着那块空格发呆,才意识到,我的毕业实习到今天,已经结束了。
两个月前,距离我大学毕业还有一季的时间,刚通过一家新闻网站实习面试的我一度在家乡、公司和学校间奔波。新闻实习生的工作是琐碎的,迅速甄别各大新闻网站和现场记者速记的信息,用文字串联起来,再重新拟了标题在网站上推送出去——这和学生时代想象中作为新闻人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激情大相径庭。可这样十分被动的过程仅仅持续了半个月,人反而习惯性得安逸起来。我隐隐地感觉到什么蛰伏在身体里东西“啵”地一下熄灭了,然后变成了一架只会发稿的文字机器,效率极高,却失了最初看到某份稿件时悲天悯人或是义愤填膺的情绪。我本是个漂泊感极重的人,大学四年酷爱着民谣和穷游。可此时心里却想着,先稳定下来吧,如果能先这样稳定下来,也不错。至少还知道离开象牙塔以后,自己的下一站在哪里。
有人带着一杯柠檬水悠悠地走到我身旁,是小满。简单扎了马尾的她面貌清丽,身上围了淡绿色的格子围裙,不属于那种倾国倾城的绝色美人,但胜在干净素雅,自然舒服,我想大抵是常和花花草草们待在一起的缘故。
她坐到我对面,轻声地说:“那次以后,你去看过青青吗?”
二
在实习半个月以后,我接到了第一个专栏任务,主人翁们来自城市边缘的一所孤儿学校。我们驱车穿过几个人声鼎沸的闹市区,往西驶了大概二十多分钟,上了一条道边栽种了许多速生杨的宽敞大路,路的另一边有几个农民赶着牛车并行,他们的身侧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田地。时值春分,播下种的作物还没从土里探出头,地平线上只有时不时竖起来的几座高矮胖瘦各不同的墓碑,孤零零地杵在那儿,像是一张油纸上溅落的墨水滴,突兀又刺眼。这样的景致持续了许久,终于看到依着几座低矮的土坡集簇的平房,整整齐齐得码在一起,阡陌交通间能看到几个坐在马扎上晒太阳的老太唠嗑。我们一行人齐齐下车,一根光秃秃的旗杆暴露了学校的所在——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根旗杆,我很难相信这破落的建筑是一所孤儿学校。锈迹斑斑的锁头和铁链锁着的大门已经很久没用过了,旁边的侧门开着,门把上拴着一只黄黑参半的土狗,懒洋洋地趴在地上。轻风拂过摇摇欲坠的死灰色围墙,有某种藤蔓类的植物枯死在上面,留下褐色的残躯,又有新的枝叶缱绻地盘上去。
“市中心不是有一所社会福利院吗?”我惊恐地对同行的摄像说,“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和流落街头有什么差别?”
摄像是个三十多岁颇具艺术范儿的汉子,扎了个半丸子头,一脸络腮胡子。他叼着根烟,不以为然地回答说:“你还是太年轻,要学习一个啊,市中心那所你得有本市户口,要街道开证明啊,现在很多弃婴出处都不知道在哪里,都只能送到这来。”
我环顾周围,同事们的表情都很淡定,显然早已有了准备,甚至还来过不止一次了,摄像大哥拿手肘怼了怼我,挤眉弄眼地说:“其实公司一直都呼吁社会各界关注这类弱势儿童的,新闻部和公益部都弄了好几波儿关爱孤儿和关注儿童心理健康的栏目,也做了大力宣传,然并卵,新闻嘛,那一阵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不过现在不都这样吗?基本上都拿慈善来博个声誉,真正做实事落到实处的有之,但很少。”
我正想说些什么反驳他,侧门里走出来一个微微驼背的中年男人,看起来颇为硬朗,走路生风,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兼老师,兼教务主任,兼门卫。事实上这个学校的高层也就只有他们一男一女两夫妻而已。嘴上说着一些官方话,和带队的主任握了手就召集我们进学校里去。整个采访拍摄过程结束得很快,学校里的十几个孩子都怯生生的,有一个胆子稍大些的,也只是眼珠子打着轱辘时不时往摄像机和我们身上瞟一圈,然后低头问什么答什么。我作为实习生任务不多,只是跟着摄像大哥做他的助手,然后对环境和孩子们进行记录。
期间我注意到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身形消瘦,头发很短,身上穿着的粉白长袖T恤上印着喜羊羊和美羊羊,领子上有一圈蕾丝,蓝底白花儿的单裤有些长了,裤脚堆在纯白色的布鞋上。她一个人靠在走廊边的柱子上,没有过来作访谈,甚至对于这里难得的热闹看也不看一眼。
我心里十分自以为是地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悲悯情绪,我心说,好可怜的孩子,肯定是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吓到了。爆棚的圣母情结驱使下,我挤出一个温暖的微笑,三步并两步地跑过去和她打招呼,但却没有得到回应,她只是定定地看着身旁的某一处。顺着她的目光,我找到了花圃灌木下藏着的一株倒伏在地的赤鬼城,徒长得厉害,有三分之一的茎都已经水化了。
“你是因为花病了,所以不开心吧?”为了解决长久的沉默间的尴尬氛围,我在她身边坐下,轻声说,“我帮你治好它吧,怎么样?”
话音刚落,她就转过脸来,眼里绽出一段绚丽的焰火。那时我才发现她有一双清亮的眼睛,其中充满满了自责和渴求,冲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心满意足地牵着她下了走廊,托大学时种植多肉经验的福,用军刀挖出那株赤鬼城,剪掉了水化的部分,然后重新整出一段茎扦插。整个过程看得她一阵心疼,我笑着对她说:“姐姐是为了给它治病,它这个部分病得太厉害了,只能切掉,否则就会感染其他的地方,到时候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明白么?”
女孩儿怔怔地看着我发愣,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眨巴了一下,忽然泪珠就断线般地落下来,我权当她是自责,连忙揽过她的身子安慰她,告诉她既然发生了就不可挽回,只能再往后的日子里主义浇水的事宜,免得再把花涝死。
她在我怀里一边点头一边抽噎着,过了很久终于开口说话,软软的嗓音很可爱。她告诉了我她的名字,董青青。
三
草木小铺外的雨势渐弱,春夏之交的阵雨就是如此,来得快去得也快,铺子里的空气充满了泥土与绿植混合的气味,很好闻。原先聚集在铺子里的人们要么打车离开,要么被接走了,要么见雨小了,顶着包或衣服冒雨前行,踮起脚尖避开水坑走路,小心翼翼一如马戏团里走钢索的人,充满喜感。只剩下三三两两几个人,在店里携友人煮着茶谈笑风生,一点也不在意天气的样子。
“最近这段时间,太忙了。等我从学校回来吧,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孩子们吧。”我接过小满递来的柠檬水,一饮而尽。
“嗯,能做的也不多。”小满望着店外的车水马龙,好似在感叹,好似在自嘲,“毕竟,孩子们都是无辜的。”
我抬眼凝视着小满的侧脸,她比一个半月前我第一次见她时,消瘦不少。
那是我认识董青青的第二天,专题采访的视频剪辑需要补拍几个镜头反映孤儿学校的孩子们生活的日常,鬼使神差之下我自告奋勇和摄像大哥同行,因为脑海里有双挥之不去的明亮眼睛,还有那株因为照顾过周所以生了病的赤鬼城。
我们到孤儿学校时,中午放饭的时间,简陋的食堂里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的味道,但这也足够孩子们兴奋愉悦,对他们来说满足实在太过简单,不过“衣敝体,食裹腹”六个字而已。可我寻了许久,却没在那些快乐的面庞里看到董青青,在不大的学校里走了一圈,还是在那株赤鬼城旁发现了她和小满。
董青青先发现了我,欣喜地拉着小满过来作介绍,她们两人都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连衣裙,在春风的吹拂下相得益彰。
“姐姐,我和小满姐姐在玩过家家,我是小赤的妈妈,小满姐姐是小赤的爸爸。”董青青拉着我的手,显得有些亢奋,告诉我因为我救了那株赤鬼城,所以可以做它的阿姨,言语之间还自顾自地轻声呢喃类似“小赤又多了个亲人,这样以后就不会孤单了”之类的话。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在三月的春光下痴痴傻傻地和那株赤鬼城对话,就连我和小满都很认真,好像它真的会答应一样。
我们一直陪着青青,一直到学校规定的午休时间,在她一脸不情愿地被驼背的校长领走以后,我和小满绕着学校的围墙散步,她在三年前第一次看到我们网站推送的关于这所孤儿院的报道,就开始为这里免费地提供绿化。虽然都是极便宜的植物,但在天真无邪的年纪看到学校里增添了绿色,特别在那些植物开花时,也足够孩子们雀跃很久。
“特别是青青,她很有灵气。”小满告诉我,青青的妈妈生前也喜欢摆弄这些花花草草,所以初见时就与她投缘,总想跟她学习草木之道。
“那她母亲是怎么过世的?”
“糖尿病。”小满垂下眼帘,折下一支路边的垂柳,淡淡地说,“说是病得两只脚都溃烂了,就和那株赤鬼城一样,各种并发症一起,神仙也救不回来。”
我一时间心神剧震,没顾得上为昨天说的话忏悔,急切地问:“那青青呢?她也病了吗?”
小满微微点头,告诉我青青是一年前病发的,那时候起她的饮食都和其他孩子分开,这一年前前后后也收到了一些善款,加上小满的一部分收入,还能撑得过去,但也快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我心底填满了疑惑,口不择言地问了一句:“那你呢,你和青青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么帮她?”
小满有略微惊诧地回头看了我一眼,旋即恢复了她淡然的常态,微微笑着回答说,“大概因为我们都是爱花的人吧。”
那时我看着垂柳下静静伫立的小满,忽然觉得无地自容起来。整个学生时代都在家庭羽翼的保护下过得一帆风顺,早已选择性地屏蔽了这世道的残酷,纵使大学读了新闻专业,却依然选择立足这世界最繁华的中心地带,谈论时局、谈论经济、谈论娱乐八卦、谈论如何运用舆论引领价值导向;纵使实习工作在新闻的第一线,却只关注个人的稳定和富足,谈论衣品,谈论妆容,谈论美食豪车,谈论如何以一代新闻人之姿立足市场经济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早已忘了一个新闻人为民喉舌的初心。
翌日我向公司申请做一个董青青的专栏,意见却被驳回,当时摄像大哥在我旁边戏谑地说,“新人啊,你还要学习一个,遵守公司章程,该怎么着怎么着,就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了。”
摄像大哥说的话我向来不太服气,可却没有丝毫办法。只能在自己的博客上记录青青的故事,期盼或许有一天会得到网友的关注。
四
接到小满的电话已经是几天之后,电话里说青青的糖尿病引发急性神经炎,忽然失明了。我赶到医院时,青青乖巧地靠在病床上吃小满喂给她的番茄。
“怎么样了?”我把小满拉到一边,轻声问她。
“送来的及时,继续治疗是可以慢慢恢复视力的。但就算这样,没有个半年也好不了。”小满说,“医生说,考虑经济状况,先留院观察一天,以后一周来两次就好。”
那时我心里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我就在青青身边,可除了微薄的经济支援,真的就一点有助益的事都做不了。站在床边的我不知如何自处,漫不经心地扫视着病房周遭的环境。
然后视线划过了病床前插着的病例卡。
董青青,男,12周岁。急性视神经炎,1型糖尿病。
“什么?!青青是男生?”我抬起头诧异地看着小满,心中的疑问脱口而出。
小满还没来得及回答,青青突然秫秫地发起抖来,颤抖着喊道:“不是的,姐姐,我不是男的!”焦虑的情绪让眼压也跟着升高,他一边失心疯般喊着,一边捂着双眼,泪珠不断从眼中滚落。几个值班护士冲进来拉起床帘,把我和小满劝了出去。在走出房门之前我还听到青青“姐姐要相信我”的嘶喊声,有些恍惚地看向小满,她依旧云淡风轻,眉眼鼻唇之间的弧度淡淡的,说话的声音淡淡的,似乎无论发生什么都无法撼动淡淡的她,宛若一口深邃的古井,你丢进一粒石子,激起几圈涟漪以后便沉入井底,不见天日。
那天她把所有关于青青的事情都和盘托出,那是发生在一个性别认同障碍的男孩儿和他糖尿病母亲之间的故事。
小满说,青青他爸很早以前就不在了,没人知道他是死了,抑或去了哪里,过着窘迫或者光鲜的生活。自青青有记忆的时候开始,便是他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他妈妈有病在身,干不了什么活。只在家里纳些鞋底挣钱,然后靠着每个月几百的低保过活。青青四五岁的时候,就表现出与常人迥然不同的个性,他似乎很讨厌自己男孩儿的身份,总在洗澡的时候,痴痴地盯着自己的身体发呆。随着年龄的增长,即使青妈是个粗人,但也看出来儿子的不同,想要留长头发,总爱穿花色的衣服,但因为身体日渐衰弱,她再没有精力去顾及儿子的心理健康,一切都顺着他来,大抵是想着不管儿子认为自己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都没关系,只盼着自己能多活一天,再多活一天,只要熬到长大成人的那一天,他能够自食其力的那一天,那时她就能安心地走了。
但天公向来不作美,十岁那年母亲的去世对青青来说是一道晴天霹雳。人没的时候,青青就在坐在床边,三伏天里同自己母亲的尸体一起待了三四天,饿得昏过去然后醒来,然后再昏过去。直到邻居闻到尸臭味来敲门才发现。
医院只负责把孩子救醒,看人没死就皆大欢喜地遣回街道,街道办公室以流动人口分配给孤儿学校的标准把青青送到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地方,那也是小满第一次见到青青的地方。从前校长和小满试着纠正过青青对自己性别的认识,但直到有一天晚上他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攥着阴茎要自残的时候,他们才认识到青青是多么无法接受自己是个男生这个事实。那以后他们便不再强求,给青青做女孩儿打扮,把他当成女孩儿来对待。
“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他是个女孩儿了,就没特意提这件事,”在医院的长椅上,小满有些愧疚。“也是今天病例打卡的时候才反应过来的。”
但又能怎么样呢,青青是个男孩儿或者是个女孩儿,真正爱他的人,一如他母亲,一如小满,都不在意这一点了,如果他能再适合自己的方式里活得快乐,那才是最重要的。
青青的情绪安定下来以后,我到他跟前和他道了歉:“姐姐没有不相信你。青青觉得自己是女孩儿,那青青就是个女孩儿。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眼睛养好,这样才能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啊,然后姐姐就从青青你的眼睛里,看你看到的世界。”
记忆里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现在已然失了神彩,怯怯地点了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明天姐姐再过来接你回学校哦,现在姐姐有些事,就先走了。”我摸了摸他的头,继而和小满道别。
离开医院就近找了家网吧,在长微博里写下了青青所有的故事,然后花了些钱买了博文热点,找了几个大V,想要迅速地把青青的故事推送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处境。
然而第二天,我得知了青青的死讯。电话那头几近癫狂的小满撕扯的嗓子,说她只是出去了一小会儿,青青就忍着疼睁开眼,循着那一点点光感走到窗边,放飞了自己。他深深地、深深地坠落在这座繁华都市的地平线上。那具小小的身体绽开了一朵血红的赤鬼城,像是宣纸上溅落的一滴朱砂红,突兀而刺眼。
五
“我要回家了。”
小满的声音没有把我拉回现实,草木小铺依旧弥漫着那股清新的泥土味道,我脑海里还回荡着她刚才说的那句“毕竟孩子们都是无辜的。”
她说的不错,孩子们都是无辜的,这也是千百年来历史长河中流荡着的话语,但历史也应证了太多无辜的人在漫长的岁月里成为时间的祭品——时光让个体通向他们唯一的、名唤死亡的归宿;时势让个体在江山美人成就颓败中沉浮跃进;时局让个体前赴后继地自觉抑或不自觉地做牺牲。难道时间不是这世上最为肆虐的暴雨吗,每个人在时间面前,都只是一粒尘埃。
青青生前是一粒尘埃,他选择结束他幼小的生命之后,也成了那些尘埃中的一份子。像他这样的人不会有墓地,人们只会把他和一批无名氏一起拉去火葬场焚化,装进那个四四方方的小黑盒子里——但他不该受这样的待遇,事实上,世间的所有人都不该受这样的待遇。青青是自由的,在他短暂而鲜活的生命里,就不曾受过性别的束缚。他在离开以后,我和小满绝不容许他被桎梏在人世间的条条框框里。我们单独为他办了葬礼,那天,孤儿学校校长夫妇在场,学校里那十几个孤儿也在场,我公司里的那位摄像大哥也在场。我们上了市里最高的山,扬了他的骨灰。
“嗯,雨停了,我也该走了。”我点头答应,站起来准备离开。
“这是青青的赤鬼城,你带走吧。”小满叫住了我,递给我一个小花盆。“我把它送给青青,感谢他让我看到他看到的世界,让我知道原来我那么幸福,世界上有太多不幸的人。”
我转过身看着那棵被我救活的赤鬼城,此时它红得那么刺眼,只听见小满继续说:“现在送给你吧,记得不要只看见世间的声色犬马,还有很多等待你去保护的人。你要做他们的喉舌。”
“你要做他们的喉舌。”
我带着青青的赤鬼城走出草木小铺,走在被这场春雨洗礼过后的街道。不时有树上的雨滴落在我的外套上。里面包含着八百万个水分子和亿万个尘埃。